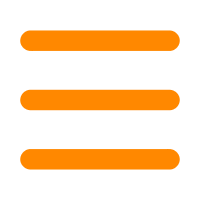在国内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关于二审的裁判方法上均设置了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规范,作为本着“有错必纠”原则、加大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监督的一项要紧程序保障,不容不承认发回重审规范在诉讼程序中发挥了肯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但因为这一规范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与实践当中理解操作不和谐,使得司法实践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因此有必要对发回重审规范进行一番重新审视。
1、现行发回重审规范的弊病
1、发回重审的规范不清楚,范围不确定。对二审发回重审的原因和标准,《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事实不了解或者证据不足的”和“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因为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从这类言语的表述来看,内容空洞,语义含混,线条粗犷,不符合法律条文应当明确、缜密的需要,给实践操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程度。对上述法律条文加以剖析,可以看出国内诉讼法对发回重审的规范规定不外乎两个方面,即事实证据上的原因和程序上的原因。事实证据上的原因基本可称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它再也找不出什么依据,因为实践当中案件千差万别,即便是相同种类型的案件,个案事实也不尽一致,而且法官的思维方法、认证能力又因人而异,那样案件事实查到什么地步即使“清”,证据举到什么程度即使“足”?现行的诉讼法没办法回答这个标准问题。程序上的原因,除去《刑事诉讼法》对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情形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外,《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不但没作具体规定,而且还赘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模糊条件“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既然是“可能”,那就是凭法官的猜测和理解,一个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是不是“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不一样的法官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判断结论。正是因为对发回重审的规范和理由规定不清楚,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有些法官借“自由裁量”之机而滥用程序权力,致使发回重审程序的不确定性和随便性,对相同种类型的案件作出不一样的处置,不只使下级法院无所适从,而且让当事人也莫名其妙,有损于诉讼程序的严肃性。
2、发回重审程序缺少稳定性。当出现发回重审事实证据上的原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二审法院既能够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当出现发回重审程序上的原因时,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则一律进入发回重审程序,而行政诉讼则同样出现了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改判的情形。这种“或发回重审或改判”的选择性程序规定,使诉讼程序缺少统一性和稳定性,即在司法实践中当出现了发回重审的情由时,并不势必启动发回重审程序。如此在理论上既可能出现发回重审过度澎涨的情况,由于二审法官可以尽量地选择发回重审程序;也大概出现发回重审过度萎缩的情况,由于二审法官可以尽量地不选择发回重审程序。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发回重审程序的价值都很难得到真的达成。这种选择性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同样会出现上述的法官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甚至滥用权力的情形而产生不好的的后果。
3、由发回重审而致使循环审判。依据现行诉讼法的规定,二审法院觉得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法定程序,则有权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法院重新作出的判决仍然是一审判决,当事人仍然可以上诉,这个时候二审法院怎么样裁判,法律没特别的规定,那样二审法院仍然有权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程序法这一非确定性标准而选择发回重审程序,案件又转入一审程序,再上诉,再发回重审……。因为发回重审的次数未遭到限制,在理论上就明显形成了“一审→上诉→二审→发回重审→一审→……”如此一个无限循环、永无止境的诉讼怪圈,案件永远在一审与二审程序之间反复运作,案件永远没办法结束,诉讼争议永远得不到解决。而且因为认定标准理解不一,这种诉讼怪圈可以套用到每一个案件中去,只须当事人一上诉,就有身陷其中的可能。实践当中确实有些案件反反复复经过多次发回重审程序,形成拉据、僵持状况,拖上几年甚至十几年不能结案。虽然这一现象在法理上无从指责,但正如有学者所说,其带来的损害是灾难性的,由于这对法院来讲不只影响到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导致有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当事人而言,不但诉讼目的无从达成,还要卷入纠缠不清的诉累中,背上沉重的经济重压和精神包袱,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会使真的的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而让清白无罪之人无辜遭到冤曲,从而损害司法审判活动的威信,动摇了民众对审判权威的信仰心理。[1]
4、发回重审规范体制上的不健全容易在法院内部产生矛盾冲突。⑴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方面,国内的审判体制决定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职责,对此上级法院应责无旁贷。但因为进入二审程序的很多案件关系复杂、矛盾尖锐,处置起来比较棘手或受外面干扰较多,一些当事人还采取了纠诉缠讼、威胁恐吓等过激手段,迫于这类案外原因的重压,一些二审法官不想也不敢让案件在自己手中作个了断,而是借机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以此推卸责任、转嫁矛盾,将矛盾的“火药桶”踢回一审法院,明哲保身减轻自己重压又不违反法律,何乐而不为?如此发回重审程序成了二审法院的挡箭牌,丧失了其应有些监督价值。这种发回重审的结果,既加剧了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冲突,又引发了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之间的矛盾,因为发回的原因不是基于案件本身、法律本身的,这就减少了二审裁判在一审法院中的威信。其次,二审法院在发回重审的内审公告中大部分已经说明要采集什么证据、查清什么事实、如何适使用方法律甚至是怎么样裁判等等,这虽然可以指导一审法院的案件审判,但更大的隐患是二审法院鲜明的建议不可防止地要干扰一审法院的审判意志,使得一审法院的独立审判原则大优惠扣。⑵一审法院内部的矛盾冲突。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需要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判,经过重新对事实进行剖析认定,重新对证据进行辩别认证,重新评议适使用方法律,新审判组织得出的裁判结论非常可能与原审判组织的裁判结论不同,也就是说新审判组织改判了初审的结论。因为大伙都是同一审判级别,原审判组织又处于被新审判组织这种表面上的监督、改判地位,在两者之间比较容易导致潜在的矛盾,也影响了一审裁判在当事人心目中的地位。
2、发回重审规范的价值考虑
作为诉讼程序的一个要紧组成部分和链接二审程序与一审程序的一项特殊规范,发回重审的规范设置应符合其内在价值,笔者觉得在重新审视发回重审时应该注意研究这方面的价值,对发回重审规范进行准确的价值定位。
1、程序正义价值。大家都知道,司法公正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诉讼规范真的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2]在目前的审判方法改革中要着重强调程序正义,来保证法官公正行使权力,并保障实体正义,公正地维护好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在重构发回重审规范时,要打造好发回重审程序的正义价值,增强其生命力。第一立法上对发回重审的规范应确定统一,获得理论与实践上的一致认识,降低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预防司法权的滥用,要体现出程序对每一个人都是公正、公平的,预防同样的案件适用不一样的审判程序。第二,程序应当维持稳定性和确定性,当出现发回重审的事由时要势必引入发回重审程序,防止选择性程序所带来的不公正性,不然两个相同的案件一个发回重审,一个改判,那样改判的案件争议会非常快得到解决,而发回重审的案件要多一个环节才能了结,对两个案件的当事人而言显然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强调发回重审的程序正义价值,甚至是允许牺牲个案的不公正来换取程序规范上的公正,譬如某被告人犯罪一审判决有罪,二审审察发现证据不足,为了追求个案实体的绝对公正,应发回原审法院查清事实,探寻证据,但从保证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程序规范公正出发,二审法院直接改判宣告无罪成效更好。
2、程序效益价值。诉讼活动的最重要目的是准时解决纠纷、解决矛盾。正如肖建国所说,程序效益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需要,它和程序公正、程序自由一同构成了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笔者觉得,这一点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同样有价值,因此,在改革三大诉讼法发回重审的程序设置时要突出效益价值,注意诉讼本钱,应当以最小的诉讼投入获得最大的诉讼产出。发回重审规范引发的诉讼过程拖沓冗长的弊病显而易见,致使诉讼周期过长,而诉讼周期过长会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当事人私人本钱的增加,二是导致法律秩序的不稳定,过长的诉讼周期会削弱当事人求诸诉讼的动机,损害法律秩序的威望与社会对司法程序的信心。[3]如此看来,设立发回重审的初衷未必能达成,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从程序效益和程序本钱角度考虑,程序不是越冗杂越好,而应越简洁高效越好,由于繁琐的诉讼程序势必要增加诉讼本钱,减少诉讼效率,所以发回重审的程序应简洁、快捷。
3、程序监督价值。发回重审规范是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推行程序监督的一项基本规范,需要体现出其应有些程序监督价值。第一,发回重审程序要便于二审法院推行监督时进行操作,也就是要具备实用性;第二,根据发回重审程序推行的监督应当准确,不可以引发不应有些争议;第三,要结实树立发回重审程序的监督权威,预防因建议不同,使一审法院对二审法院的监督产生合理怀疑,失去对二审程序监督的信赖。
3、发回重审规范的重构
基于上述对发回重审规范的弊病剖析和价值考虑,有必要对这一规范进行重新建构:
1、重新界定发回重审的规范和理由。
⑴取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一发回重审的事实证据上的规范和理由。
长期以来,国内的审判活动一直强调“以事实为依据”这一基本的司法原则,需要审判活动尽量地发现、挖掘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谋求实体上的绝对公正。理智地深思一下,大家就会发现这一原则存在着致命的缺点。案件事实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探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事实上是通过目前的证据去再现已经发生过的案件事实或案件发生的过程。[4]但因为时间的不可逆性、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审判职员辨别思维方法的差异性,完整地再现过去的客观事实则是一种不可达成的空想。有学者还觉得,“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事实上也与现代的证明责任规则不相符,当案件处于真假不明时,法院应依证明责任规则作出裁判,而无权对此拒绝审判。[5]诉讼活动不是一个认知过程,而应是一个证明过程,不可以像搞科学研究那样探求客观事实的绝对化,而应根据程序公正的原则证明法律事实的合法化,这才是程序的价值所在。因此,从诉讼活动的客观规律出发,笔者觉得“以事实为依据”的说法不应倡导,可以将这一原则重新表述为“以证据为依据”。
但受“以事实为依据”原则的影响根深蒂固,国内二审法院在对一审判决进行审察时比较看重案件事实证据方面的审察,“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就成为发回重审的一个要紧理由。但这个理由的缺点十分明显,对这一理由的批判有一段十分精彩的二难推理:假如二审审理中已经查清了案件的事实,并据此断定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那样,不对案件直接改判而发回重审,岂不画蛇添足?假如二审审理中并未查明案件的正确事实和了解事实是什么,怎么样能得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的结论?凭什么把案件发回重审?[6]笔者觉得,否定发回重审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个标准至少有四个理由:第一,这个标准带有过分的自由裁量性质,换句话说,也就是非常强的不确定性。对案件到了什么程度和地步才是事实了解、证据充足,二审法院和一审法院可能各有其不一样的认识和理解,即便在一审法院内原审判组织和新审判组织之间也会存在差异,事实上也非常难评说哪一种认识和理解孰是孰非,那样最好就由二审法院依终审权力直接进行断定,不适合再发回重审,不然,既不可以准时解决纠纷,浪费司法资源,又损害法制的一致性、统一性和相对稳定性。第二,这个标准有悖于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司法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案件事实查到什么地步,不是由法官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当事人的举证程度,因而二审法院以这个标准发回重审,未免有将本应由当事人承担的责任转嫁由法院承担之嫌。第三,这个标准也存在二审法院先入为主之嫌。二审假如觉得“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事实上是基于存在这个案件事实的推定,先入为主地将案件置于什么场景之中,也就是从事实到证据的逻辑过程,而不是从证据到事实的逻辑过程,这种做法显然不妥,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这种推定与“无罪推定”的原则恰好相反。第四,这个标准仍是在鼓励一审法院主动、积极地调查案件事实,越俎代庖地介入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甚至是站在一方当事人的立场调查取证,不然,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会被发回重审。这仍是职权主义法律思想的体现。
⑵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应一律发回重审。如前所述,国内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对程序有问题的案件发回重审时强调“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行政诉讼中对程序问题还可以改判,刑事诉讼中虽然对发回重审的程序问题具体化,但仍不够到位,而且也体现了程序问题要达到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可见,国内诉讼法对发回重审的程序性问题采取了低标准的态度。如此,一些一审判决虽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但并不被发回重审,甚至通过终审审判而被合法化,因而如此的程序标准是“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在法典中的典型表现。[7]如此,实体结果的正确性掩盖了对程序正当性的需要,无异于在暗示甚至鼓励法院及其法官可以在肯定限度内不按法定程序办案,且免受任何追究,[8]势必会损害程序法的地位和价值,程序公正很难得到真的达成。所以,程序违法无大小,只须一审判决违反了法定程序,无论是否会干扰公正审理、正确判决,都应当通过启动发回重审程序确认其无效。而且程序违法是过程违法,判决却是实体裁决,用实体办法来解决程序问题并不是良策,因而程序违法不适合通过改判方法来解决。
⑶舍弃实践中“适使用方法律错误”、 “判决不当”等任意性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适使用方法律错误”、“判决不当”等理由屡屡见诸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这混淆了发回重审和改判的界限,也是权力滥用的表现,将这类非法定事由随便引入到发回重审程序中,只能致使这一程序的秩序愈加紊乱、威信愈加减少。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适使用方法律是不是正确、判决是不是适合等问题完全负有监督职责,应当通过改判程序来纠正一审判决中的类似问题。
2、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严格的限制。
因发回重审而引发的无限循环诉讼怪圈,确实风险相当大。但只须承认当事人对重审后的判决享有上诉权,而且发回重审的次数又不加限制,这个诉讼怪圈就仍然会存在,那样从机制上终结循环诉讼的方法有两个,一是不允许当事人对重审的判决再上诉,二是限制重审次数。前者显然不可取,不承认重审后由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一审判决明显违背两审终审原则,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一定当事人对重审后的一审判决仍然享有上诉权,所以对发回重审的次数加以限制是终结循环诉讼的惟一方法,事实上这个方法是可取的、便于操作的。笔者觉得,对三大诉讼法发回重审的次数在立法上限制为一次即可,由于二审法院审察发现一审判决存在发回重审的事由时,给予一审法院一次重审机会,一审法院就应当注意到问题的存在而加以纠正,但若一审法院未作纠正,则说明一审法院或者不觉得存在错误,或者不愿纠正,或者无力纠正,那样给予再多的重审机会也无济于事,反而不可以飞速解决争议,致使诉讼本钱的成倍增加、诉讼效率低下。
3、正确、妥善地适用发回重审规范。
⑴二审法院应依法行使发回重审权。发回重审是由诉讼法规定的一项诉讼程序,二审法院只能依据法律行使发回权,不然依法律以外的原因行使这项权力,就是不依法审判而滥用权力,不可以保证法律程序的严肃性。实践中,发现有些上级法院在诉讼法以外拟定了一些内部的条条框框,需要下级法院需要遵守,不然案件一上诉就发回重审,这种非依法监督制约的手段是不妥的。
⑵重审判决应注意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相衔接。上诉不加刑原则是刑事诉讼中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有益手段,假如重审判决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就会违背被告人的上诉愿望,上诉权益得不到保障,只能会让被告人慑于上诉。因此,笔者觉得,重审判决应考虑上诉不加刑原则,确要加刑的则应通过再审程序加以解决。这一法律思想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同样应得到尊重,即在重审时防止加重上诉方的责任。
⑶废止再审中的发回重审程序。依据最高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建议的规定,人民法院提审或根据第二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原1、二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裁定撤销原1、二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该规定在二审的再审程序中启动发回重审,将案件直接转入一审程序,由一审法院来纠正原一审程序的错误和二审程序的错误,这一做法欠妥。况且,案件到了再审程序,已经费了很久,再发回重审反复运作,必然会愈加拖长审判期间。因此,笔者建议取消再审中的发回重审程序。
参考论著:
[1]周利发:《论发回重审的次数限制原则的打造》,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2]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健全诉讼规范》,转引自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3]肖建国:《程序效益论》,载《诉讼法论丛》1998年卷。
[4]张卫平:《民事审判与事实探知的相对性》,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5]参见金友成主编:《民事诉讼规范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6]蔡晖:《对认定事实存在问题的案件不应发回重审》,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2期。
[7]参阅毕玉谦主编:《民事诉讼判例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8]赵钢:《正确处置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十大关系》,转引自同[2]。
重新审视发回重审规范
点击数:515 | 发布时间:2025-06-20 | 来源:www.36001.cn
- THE END
声明:本站部分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如不慎侵害的您的权益,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
-
- 学习交流 -
-
欢迎加入国家人事考试网,与万千考友一起备考

- 成考路上不再孤单
专业院校
-
关注“考试直通车”
-
领取备考大礼包
-

点我咨询
返回顶部
Copyright©2018-2024 国家人事考试网(https://www.scxhcf.com/)
All Rights Reserverd ICP备18037099号-1

-

国家人事考试网微博
-

国家人事考试网